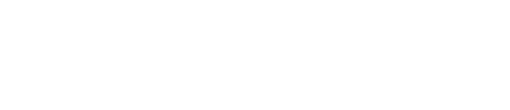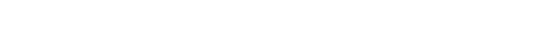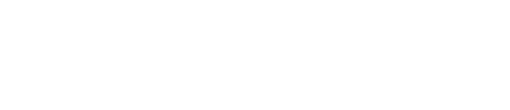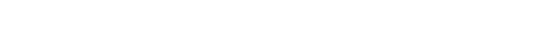时事的演进,有时像一个怪异的顽童,说不定一个什么偶然的契机,便会使他对已然逝去的往事突然追思和兴奋起来。接受全新社会变革的中国人,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物质生活的丰富化,使他们逐渐摆脱了苍白与窘迫。
上世纪90年代的一天,读者突然在书摊儿发现了一本书:白色的封面上印着一张毛泽东与女儿李讷在一起的黑白照片,粗重的圆头字标出书名——《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较之那些哗众取宠的书刊,这本书无论在装帧和印制上都很难产生书籍出版者所期待的那种“60秒效应”。然而,当人们信手拿过这本书,便再难以把它合上:一个血肉丰满、像普通人一样有着七情六欲的,一个也会哭也会笑、也爱开玩笑、也爱吃红烧肉的,一个过去被罩上了一身灵光、圣洁得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终于从人造的祭坛上走下来,慈祥如父兄,亲诚像挚友。
《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风靡图书市场,一时洛阳纸贵。现在,几乎谁也说不清它的印数到底是多少了。因为除了出版社正常的印制外,唯利是图的书商们大量偷印盗印,如果从这本书的影响所及分析,印数在200万册以上当属于比较保守的估计。
读者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书的封面上一个颇具特色的名字——权延赤。
名字是一种符号。但父母在为子女起名时,又总是寄托了某种情思或是反映了一种特定的时代环境。“延赤”这两个字的组合,便是他父母革命生涯的写照:孕于延安,生于赤峰,长于赤峰和呼市,一条典型的塞外汉子。生他时,早年即参加革命的父亲已是二十军分区的政委,而13岁便参加革命活动的母亲则担任着区妇联主任职务。权延赤记事时,父亲已经在某省出任省委秘书长,不久又担任了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应该说,他幼时的生活条件是相当优越的。
冷酷也许常常是温情的守护神。
12岁的权延赤还理解不了这个道理。有一天他默默地走进父亲的办公室,接受了父亲的又一个近乎“残酷”的决定——从即日起,到学校食堂入伙。复杂而深沉的全部理由,父亲只用一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话便概括了:“你该吃学校的食堂了。”
好容易盼到学校放暑假,权延赤以为可以在家改善一下生活了。不想,父亲又把他叫进办公室,说:“我在你这个年龄,已经离家出走了,你母亲也是13岁便参加了革命。你这么大了,还没经过什么风雨,也不懂得生活的艰辛,你到农村去吧!”
从此,几乎所有的假期,权延赤都是在农村度过的。在农村,他最愿意干的活就是拔麦子和掰老玉米。拔麦子尽管极苦,但是拔一把可以吃一口;掰老玉米就更有诱惑力了,饿了,啃一只嫩玉米棒子,又香又甜,真是美极了。有时候,他甚至连玉米芯也嚼巴嚼巴吞进肚里。
有一年暑假,权延赤所在的农村断盐。七天不尝咸滋味,直馋得他一口一口去喝老乡家腌菜的汤。盐有了,权延赤挖来一大盆野菜,把盐压碎,细细撒在上面,吃个精光。盐搁多了,吃完了便喝水。于是,他又一缸子一缸子地灌了一肚子凉水。夜里,便上吐下泻,浑身浮肿,眼睛只剩下细细的一道缝。权延赤好容易睁开眼,见父亲正站在床头,默默地望着他。老与少,两段物化的历史;两个人,延续着同一条生命。
“今天,我特别感激我的父母。现在,我可以适应最艰苦的生活,就是得益于他们当初的爱。爱有两种,一种是溺爱,一种是慈爱。所幸,我得到的是后一种爱。不然,今天我也许会成为一个纨绔子弟!”“有人之所以狂妄自大,就是因为他父亲从小对他娇生惯养,肆意放纵所致。这样的人走上社会,十个有五对要摔跟头!”
“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诚如斯言哉!
权延赤大学毕业后,应征入伍,满以为自己是一匹骏马,可以有一块纵辔驰骋的草原;自己是一只雄鹰,可以有一方展翅翱翔的蓝天。不想,“文革”风暴中,担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的父亲被打倒在地,从此,权延赤在政治上被划归了另册,那一块草原、那一方蓝天便似乎渺茫了。
他成了“勤杂工”:接兵、送兵、买器材、下农田、带宣传队,就是始终不能接触业务。搞数理化比不得挥文弄墨,长期荒废再想捡起来就难了。权延赤心急如焚,又无可奈何,只好借酒浇愁,吟诗解闷。刚烈一条好汉,禁不住泪如雨下,大放悲声。
冥冥中似乎听到有人在冲着他的耳朵喊:“权延赤,我告诉你!酒精只烧数学脑袋,不烧文学脑袋,你写东西吧!”这声音,在权延赤的耳畔一直回响了一夜。
可是,“文革”浩劫,找本书学习又谈何容易?费了好大劲,翻箱倒柜才找到一本马烽的小说集:《我的第一个上级》。这本书没头没尾,中间也有一些被撕去派了别的用场,只有《韩梅梅》一篇是完整的。权延赤以异常虔诚的心境重新读了几十遍。琢磨它的谋篇布局、起承转合、语言特色和思想的发展脉络,一句一句地抠,一字一字地想。读第一遍时,似乎读懂了,可是读到第七八遍又糊涂了,读到二三十遍时突然茅塞顿开,觉得一下子豁然开朗起来。他长叹一口气,把书一扔,道:“我也能写!”
他利用病假的时间,关上门,铺开稿纸,写下了小说的题目:《新来的女大学生》。写了撕,撕了写,整整两个月,头发不剃,胡子不刮,饿了,煮一把挂面,渴了,喝一碗凉开水。直写得昏天暗地,脸如青灰。小说写好后,他仿佛大病一场,一脸络腮胡子长得老长,远远望去,犹如刺猬一般。
部队在山西,于是他就想当然地在信封上写上了:太原《山西文学》几个字。稿子寄出后,权延赤坐立不安,茶饭不思,像是待决的囚犯在等待法官的宣判。
五天后,在内蒙古出差的权延赤接到了通知他去山西《汾水》编辑部的电话。
放下电话,权延赤找出一瓶汾酒,就着半个干馒头,美美地喝了一顿。随后,星夜南下。没买到卧铺,他一天一夜没睡觉,到了太原仍然精神焕发,只觉得天也高了,地也阔了,连街市上的一张张陌生面孔,看上去也叫人想乐出声来。
从此,权延赤开始了他那辉煌而又艰辛的文学之旅……
《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是权延赤的成名之作。这样一部十几万字的小册子所产生的影响,绝非笔者能够阐述清楚的。也许,估量它的价值,将是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事。这里我要告诉读者的是,它最早的成因完全出于一次偶然的机遇。
1986年,在北行的列车上,躲出北京去创作长篇小说《多欲之年》的权延赤正好与一位空政文工团的演员同行。
机遇,如稍纵即逝的火星,你得到它了,便可以点燃事业的熊熊烈火;没有得到它,火星逝去,你的生活会仍如往常一样平淡。
或许是这位演员曾拜读过权延赤的作品,或许是他的真诚和豁达容易消除心与心之间的隔膜。她讲述了自己的见闻、自己的经历,讲她当年陪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跳舞的故事。良好的悟性和作家的敏感使他意识到,这里有丰富的宝藏,值得下大力气去掘一口深井。
就是在这个时候,一个思想在他的头脑中逐渐清晰了,一个心愿也悄然埋入心底。作为投石问路,权延赤回到北京后写了一篇8000字的纪实文学,后来文章以《珍藏在心底的回忆》为题在《追求》1987年第3期发表后,反应强烈,随即被《读者文摘》等十余家报刊竞相转载。
这以后不久,被人为供上神坛的毛泽东的形象就通过李银桥等贴身卫士们的娓娓讲述和权延赤手中的笔,走回了生他养他,和他休戚与共、血肉相连的亿万人民之中……